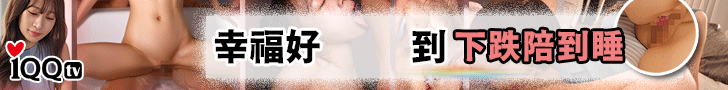見阮夢玲不出聲,他更堅定了自己的判斷,到廚房抄起一把菜刀就往出沖。
阮夢玲跌跌撞撞的從床上爬起,一把摟住方強的腰。
「…強子…聽我一句…咱算了吧…咱馬上就要…別為了這個事…」
方強低頭去掰阮夢玲雙手,卻見她一隻手上幾隻指甲竟都脫落,顯然是掙扎之時奮力抓撓所致。
胸中更是怒火中燒,熱血上湧,一把甩開阮夢玲。
阮夢玲一聲驚呼倒在床上,方強怕她摔傷,回頭去看,卻見她屄內流出的灰白精液掛在腿上往床單上滴落。
見方強拿了刀衝出去,阮夢玲就知道要壞事。
但她這個樣子實在沒法跟出去,待披上衣衫,追出家門,方強早就沒了影子。
那一夜,方強拿著一柄菜刀衝進老葛家,揮刀亂砍,葛老二父母妻兒全都死於刀下,唯獨葛老二當夜睡在廠子裡,逃過一劫。
夫妻倆連夜逃到山裡,躲了兩天,才尋到一個機會出了鎮。
一路上躲躲藏藏,好不容易才到了集合地點,憑陳老三安排上了船。
*** *** ***
阮夢玲是被人敲打集裝箱的梆梆聲吵醒的。
集裝箱裡黑乎乎的沒有一絲光亮,她只能聽得出,聲音是在離她不遠的地方,那人敲一陣,停一陣,嘴裡咒罵不止,聽聲音似乎是個女人。
「那騷狐狸又來了。」方強在阮夢玲耳邊嘀咕著,引得阮夢玲一陣無聲地笑。
騷狐狸是方強給那個濃妝豔抹的女人起的諢名,上船的時候,女人大多素面朝天,衣服也多是寬鬆合體就好,唯獨她濃妝豔抹,衣裙華麗,單只她手腕上那塊名表,就是一般人家十年不吃不喝都買不起的。
「肯定是哪個有錢的,當官兒的人的情婦。」方強蓋棺定論,阮夢玲深信不疑。
他們現在所處的這個集裝箱,是這艘貨輪堆放的眾多集裝箱中間的一個,進出只能將集裝箱的門打開一條小縫,側著身子出去,然後在眾多集裝箱的縫隙裡一點一點的挪出去。但此刻,就連這道只能打開這一條小縫的門,也被牢牢地鎖住了。
他們,就像是囚徒。
「老娘給了你那麼多錢!你就讓老娘睡在這鐵盒子裡?」騷狐狸用手中的高跟鞋大力的敲擊著集裝箱的鐵壁,累得呼哧呼哧直喘。
「別他娘的敲了!讓不讓別人睡覺?」一個男人氣惱的搶過騷狐狸的高跟鞋,罵道。
她女人懷著身孕,妊娠反應加上暈船,折騰了許久,好不容易才入睡,就被騷狐狸敲打集裝箱的聲音吵醒。
「老娘願意敲,你他媽管得著嗎?」騷狐狸像是受不了集裝箱的味道,用手捂著鼻子,甕聲甕氣地回了一句,又脫下另一隻鞋翹了起來。
「算了,別跟她置氣。犯不上。」懷孕女人勸著自己正要發作的男人,在他耳邊小聲嘀咕了幾句。
男人哼了一聲,擁著女人往邊上挪了挪,來到了方強夫妻倆身邊坐下。
阮夢玲見她懷著身孕,就拿下披著的毯子,想把自己的毯子給她。
那女人說什麼也不肯,直說上船的時候,一個別人叫他老張頭的船員已經特意給了她兩條毯子。可拗不過阮夢玲,只好接了過來。
女人之間話題自然就多,兩個女人湊在一起,嘰嘰喳喳,不一會兒就聊得十分投機。那女人姓劉,大阮夢玲一歲,阮夢玲乾脆就叫她劉姐。
外面的暴風雨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停了,貨輪也不再來來回回的搖晃。
集裝箱的門被打開,門縫裡射進刺眼的陽光。偷渡客們都不禁眯起了眼睛。
「給你們一個小時時間,出來透透氣吧!別他娘的憋死了!」陳老三的聲音從門外傳來。
偷渡客們發出爆炸般的歡呼,他們爭相從狹窄的門縫擠出,來到貨輪的甲板上,情不自禁地呼吸著新鮮空氣,感受著潮濕的海風。
兄弟倆一出集裝箱就脫力一般的坐在甲板上,大口喘著氣。
「哎媽呀,可憋死我了。」
「瞅你那點出息。」
大柱子罵了一句,溺愛地摸了摸弟弟的頭,從口袋裡掏出一個精巧的鐵質煙盒「哥,我就知道你還有存貨,我都斷糧好幾天了,你也不說救濟救濟老弟。」
哥哥麻利的捲好煙捲扔給弟弟道:「這煙葉還是出來的時候,咱爹給裝的,家裡的味兒,抽一次少一次嘍。」
聽了哥哥的話,二柱子喜悅的神色也暗淡了下來。
哥倆點燃煙捲,怔怔地望著遠方出神。
人就是這樣,在家鄉久了,總是希望可以浪跡天涯、闖蕩四方。可一旦離家遠行,心中又常常懷著對家鄉的依戀和想念。
自願出門的人,甚少例外。而為了一些事情逃離自己家鄉的人,在逃離壓力所帶來的短暫喜悅之後,會不會湧起一股濃厚的思鄉之情?
「我們真的出來了,噢——」阮夢玲蹦蹦跳跳的叫喊起來,歡樂地像個頑童。
方強也開心的追在她身後,只是他瘸著腿,怎麼也走不快。
「嘿!你!」
一個身高足有一米九的黑人船員出現在阮夢玲面前,操著一口生硬的漢語說:「別亂跑!」
阮夢玲嚇了一跳,呆呆的望著這個滿身隆起肌肉,如黑鐵塔一般的壯漢。
方強快步追了上來,一把將阮夢玲護在身後,壯著膽子問:「有什麼事嗎?」
黑壯漢似乎很不滿方強擋住了他,他隨手一推,方強就一個踉蹌摔倒在一邊,他上前一步,站在阮夢玲面前,眼睛在阮夢玲身上來回打量,說:「美麗的女士,請不要在甲板上亂跑,這裡風浪很大,會出現危險的。」
阮夢玲被他嚇得一動不敢動,只覺得他是那麼高大,彷彿已經擋住了明媚的陽光,用陰影將自己覆蓋了。
就在阮夢玲不知所措的時候,一個上了年紀,駝著背的老年船員走了過來,沖黑壯漢說道:「比利,他們還等你喝酒呢。」
黑壯漢看了老年船員一眼,惡狠狠的往地上吐了一口吐沫,扭頭走了。
「大叔,謝謝您幫我們解圍。」
方強被阮夢玲扶著站起身,向老者道謝。
「這有啥可謝的。」老者看了兩人一眼,像是有什麼煩心事似的皺緊眉頭,接著長嘆一聲,步履蹣跚的走了。
一個小時的時間轉瞬即逝,他們又再次回到那個黑暗潮濕,滿是異味的集裝箱。
令阮夢玲奇怪的是,那個騷狐狸並沒有回來,他們在甲板上透氣的時候,她似乎看見那個女人正在和船員爭執著要去見陳老三。
集裝箱的鐵門再次關閉,狹小的空間裡擠著幾十個男女,這裡沒有照明,沒有娛樂,他們只能靠睡覺和聊天來打發時間。
那些相熟的,相鄰的偷渡客們,都試探性的和身邊的人交談著,話題天南海北、葷素不忌,或高談闊論或低聲細語。
「有錢人就是了不起啊,去美國也能有特別待遇。」阮夢玲提起騷狐狸沒回來的事兒,酸溜溜的說。
「有兩個錢,臭顯擺唄。」劉姐倒是不以為然,伸手拉了拉身上的粉紅色孕婦裝道:「她這樣的我見多了。我啊,錢都給我兒子存著,讓他以後日子過得舒舒服服的……」
聊了一會兒,劉姐乏了,就披著毯子睡了過去。
阮夢玲只好和方強擠在角落裡,小聲地聊著天。
「等咱到了美國,咱也要賺好多好多錢。」
「嗯,好。」
「咱們也要買好大好大的房子。」
「行聽你的。」
「然後生一大堆娃娃。」
「嗯恩。」
阮夢玲見方強心不在焉,氣急道:「你是不是嫌我髒?我要是嫁個有能耐的,他葛老二……」
說著就捂嘴哭起來,方強只得在一邊勸個不停。
正勸著,集裝箱的門再次打開,一個船員站在門口喊道:「阮夢玲,在哪兒呢?」
阮夢玲聽到有人喊她的名字,不由一愣,方強倒是先反應過來:「在這兒呢,什麼事兒啊?」
那船員也不搭茬,捏著鼻子走進來,用刺眼的電筒光照了照方強和阮夢玲。
「你叫阮夢玲?」
阮夢玲縮了縮身子,還是本能的點了點頭。
那船員一把抓住阮夢玲的胳膊把她拉了起來,「走。」
方強扶著集裝箱的鐵壁站起身,「這是去哪兒?」
「帶她去享福。」那船員一把將阮夢玲從集裝箱的門縫裡推了出去。
方強又要開口,卻猛然挨了一記耳光。
「少他媽給臉不要臉。」
常年跑船在外的船員,身體大多強橫,這一記耳光,打得他眼前金星亂閃,耳中嗡嗡不止。
「肏你媽的,裝什麼犢子!」
大柱子二柱子見方強挨打,立刻跳了起來。
方強僅剩的血性被激起,此刻又有人幫忙,膽氣自然更足,一把抓住那船員領子就想動手。
那船員自然不肯吃虧,拍開方強的手,一腳踹在他小腹上把方強直接踹倒在地。兩兄弟見狀罵了一句就要開打,卻被身邊的偷渡客緊緊抱住,連聲勸他們不要衝動,別惹事。
兄弟倆掙了幾下脫身不得,只有罵了兩句過過嘴癮。
那船員吐了口痰,才轉身出去,關上集裝箱。
「你拉著我幹啥?你是不是爺們,咋就不敢跟他們幹?」大柱子甩開摟著自己腰的劉姐男人罵道。
「跟他們幹,拿什麼乾?」劉姐男人喘著粗氣道:「咱們現在叫他們鎖在個鐵箱子裡,而且是偷跑出來的,人家說宰了誰就宰了誰,弄死你,你都沒地方伸冤去!」
大柱子愣了一下,罵了句娘,狠狠一拳打在集裝箱的鐵壁上。
劉姐拉了拉她男人的衣袖,劉姐男人會意,兩人挪到集裝箱最遠離箱門的角落裡去了。
「小夥子,別亂來。」
一個中年人扶起方強,道:「他們常年做帶人去美國的買賣,從來不把咱們當人,只把咱們當成是蛇,是豬。」
「可我媳婦兒……」
「都要經歷這個,要在海上漂三個多月呢,他們想女人了,都會找偷渡客解決。同村的人說,這是必經的一遭……」
聽了他的話,方強的一顆心沉了下去。
阮夢玲被那船員領著再次回到了甲板上,暴風雨過後的天空如水洗一般乾淨,天邊幾朵雲彩伴著已經一般落入海中的夕陽,泛著鹹味的海風讓阮夢玲精神為之一振。
方才她聽到了集裝箱內的聲音,也知道定是方強為了自己和那船員起了爭執,她剛想轉身回去的看看,就被迎面走來的船員一把抓住,阮夢玲出聲詢問,那個船員也不答,只悶頭拉著她走。
才一進船艙,阮夢玲迎面就看見陳老三。
「貓尿狗騷的。帶她去洗洗!」陳老三皺了皺眉道。
船員應了一聲,拉著阮夢玲到了一個小艙,供她梳洗。
雖然艙內只有小半桶的水和一條硬邦邦的舊毛巾,但生性愛潔的阮夢玲還是細細地擦淨了身體。
梳洗完畢的阮夢玲讓陳春生眼前一亮,雖然她因為連續數天沒能好好休息吃飯而顯得有些憔悴,但那天生的美人胚子還是誘惑得陳春生直流口水。
船一離開港口的時候,陳春生就心急火燎地問三叔,啥時候能把阮夢玲叫過來。
三叔打了他個腦蹦,只說了兩個字:「等著!」
滿打滿算的等船到了公海總該行了吧,可又遇上了暴風雨,陳春生被顛簸得七葷八素,腸子差點沒吐出來,這剛剛緩過勁兒來,就又跑去找三叔。
所以當梳洗完畢的阮夢玲被人引著來到他的船艙的時候,他幾乎是從船上跳起來的。
「快坐快坐。」
雖然陳春生早就按耐不住想把阮夢玲就地正法的心思,但他還是沒敢像三叔跟他吹牛的時候講的那樣扒了褲子就上。
在三叔的嘴裡,那些成天做著美國夢的娘們簡直比雞還不如,只要他想了,就會從船上的人蛇裡挑出個看著順眼的伺候自己,完事兒了,再丟回去。
而最讓三叔唸唸不忘的,是幾年前三叔帶出去的那一撥人裡的幾個女大學生,每次三叔跟陳春生吹噓的時候,都聽得陳春生火氣直冒,雞巴硬得把褲子都要頂個窟窿。
所以這次他暗自下狠心,一定要肏個夠本。
可如今到了船上見了阮夢玲,他反倒慫了。
陳春生打小就是個不安分的主兒,又有陳老三嬌慣,更是頑劣得很。逞兇斗狠,吃喝嫖賭沒有他不敢幹的事兒,這幾年也睡了不少女人,從風韻猶存的少婦,到沒出校門的學生,卻惟獨沒遇見過這種女人。
面前的女人才清洗過,雖然日子貧苦,顯得清減了幾分,卻透著一股出水芙蓉般的純淨,,那眉眼、那身段,都叫他越看越是喜歡。
正瞧著,那女人對他尷尬一笑,雖然笑的勉強,卻引得陳春生心臟一陣亂跳。
他也不知自己究竟是犯了什麼癔症,竟然對這個女人如此著迷,一時間竟手足無措起來。
陳春生暗罵自己沒用,這麼下去,自己豈不是鎮不住這個女人?以後得想個法子嚇嚇她,才能讓她對自己死心塌地。
眼前的半大小子臉漲得通紅,嘿嘿傻笑著一個勁兒的獻慇勤,可他褲襠裡支起的帳篷卻早就表明了他的心思。
她訥訥地坐下,身體縮成一團。
陳春生見她也不說話,自己自然也就白話不下去了,一咬牙就貼她身子坐下,手搭上她的細腰,溫香軟玉摟了個滿懷。
阮夢玲頓時一驚。
那日在賓館見到陳春生的目光,她就知道這半大小子對自己有那心思,但去美國心切,也就沒多思量,可不想今天就應驗了。
阮夢玲忙掙紮起來,一邊推搡著陳春生,一邊軟語相求。
陳春生雖然早就想得不行,卻也不想用強,那樣不免少了許多情趣。
他嘿嘿一笑,一把抓住阮夢玲一邊乳房用力揉捏著,湊在她耳邊道:「我知道你們兩口子窮的就快當了褲子,咱打開天窗說亮話,這三個多月你把我伺候好了,我就免了你們倆的分期,這買賣劃算不?」
見阮夢玲聽了一愣,陳春生大手就順著她衣襟伸了進去,在她光潔的皮膚上來回摩擦。
「…你…你說真的?」阮夢玲壯著膽子問了一句。
「當然。」陳春生正在她身上撫摸揉捏,頭也不抬地道。
阮夢玲被他摸索撩撥得起了一身雞皮疙瘩,恨不能立刻抽身出來,可他許下的條件,卻又讓她不忍拒絕。
自己橫豎逃不過這一遭,如今點頭還能免了分期,怕是錯過了這個機會,以後再想提也難了,自己早已經不乾淨了,就是跟他睡了又能怎麼樣?
免了這筆錢,他們夫妻倆在美國就能少幹好幾年,她就能盡快賺足錢,然後把爹媽,還有弟弟也給接過來……
女人有時候就是這樣,在感性思維的驅使下,總以為犧牲自己能換來什麼,卻往往忽略了最根本的問題。
阮夢玲思量了一會兒,長嘆了一口氣,似是做了決定。
陳春生也不多言,幾把就將她剝成了白羊,一雙大手在她身上細細撫摸良久,才戀戀不捨的將手從她胸前一會兒乳房上挪開。
阮夢玲赤身弱體的躺了下來,兩條白生生的長腿向兩側分開,胯間一個黑黝黝的半大小子正聚精會神的觀察著她的下體。
她羞答答的閉著眼睛不敢去看,心裡撲通撲通的如同打鼓。上次失身葛老二,實屬被迫,沒有一絲床笫間的歡樂。這回主動分開雙腿,供人淫樂,又是一種不同體驗。
阮夢玲只覺得男人趴在她兩腿間,端詳著腿心裡那兩片嫩肉,兩隻手按在她大腿上,輕輕的摩挲,卻又感覺不到他和自己胯間有任何接觸,難道只是看著好玩?
阮夢玲正納悶間,忽覺一股熱氣吹在他的陰戶上,熱烘烘,癢酥酥的。
她渾身一陣哆嗦,那緊閉的花苞竟也抽動了兩下,滴出幾滴花蜜。
陳春生看著有趣,連吹了幾口,又用手輕輕揉弄。
誰知才一觸手,阮夢玲就低低發出一聲呻吟,發覺自己失態,她困窘間忙用雙手摀住通紅的臉蛋。
見她模樣有趣,陳春生不禁玩性大起,分開兩片嫩肉,用手指輕輕在屄裡抽動。
感覺到異物入侵,阮夢玲本能的想併攏雙腿,卻反倒把陳春生腦袋夾在中間,陳春生一口咬在她大腿上,嚇得她身子一顫,剛想躲開,才發現他只是玩樂,並沒用力。
陳春生笑道:「這麼好的一雙腿,我哪捨得咬啊。」
說罷,又用手狠狠插弄幾下,就急忙解開褲子,露出一條直挺挺的雞巴,笑道:「你這屄真白淨,好多小姑娘都比不上…嗯…還…真緊…」
說話間已經提槍上馬,那一條粗壯的雞巴已然大半捅進阮夢玲的屄裡。
阮夢玲聽他調笑,也不回答,低低叫了兩聲,像是回應,只是刻意壓抑,將聲音堵在喉間。
陳春生也不氣惱,覺得阮夢玲羞羞答答,期期艾艾的樣子有趣的很,摟著她一雙長腿又親又吻,抽插幾下,感到屄中一片火熱,那些嫩肉層層包裹,如同活物一般輕輕蠕動,不免興起,大開大合的肏了起來。
陳春生仗著年少,兩個多月未嘗肉味,對象又是自己覬覦多時的阮夢玲,自然毫不留力,使上十二分力。
床板咯吱咯吱的發出快節奏的響動,阮夢玲的叫聲也漸漸的高了起來,屄裡淫水也充沛的流了出來。
阮夢玲被他壓在身下,只覺得自己身子都快要被他壓扁了,陳春生才一把將阮夢玲抱了起來頂在艙壁上,扶著屁股從後面進入,滿是肌肉的小腹撞擊在她肥美的臀肉上啪啪作響。
阮夢玲嬌軀癱軟,抖個不停,陳春生正漸入佳境,摟著她的屁股肆意沖頂,忽然覺得屄中一緊,雞巴竟似被狠狠套住,動彈不得。
而阮夢玲也嬌媚的叫了起來,身體驟然繃緊,兩手高舉扶著艙壁,昂著頸子,活像一隻高傲的白天鵝。
從餘韻中醒來,阮夢玲迷迷糊糊的感覺到那根火熱的東西竟然還插在自己體內。
「我問過三叔了…那方瘸子…吃喝嫖賭…身子早就不行了……」陳春生一邊狠狠抽動,一邊伏在阮夢玲耳邊道:「不過我不一樣…嗯…」
阮夢玲聽他提起丈夫,心中一陣抽動,難過得閉上了眼睛,歪過頭不願看他。
陳春生偏不隨她願。
扳著她的頭臉對著自己,先痛吻個夠,飽嘗阮夢玲的唇舌,又隨著抽插節奏不停的念叨著:「看著我…看看誰在肏你…」
阮夢玲在陳春生的艙裡呆了一天一夜,期間兩人除了吃飯外都膩在一起。
看著阮夢玲離去時,滿臉的羞憤,陳春生只覺得心情大好。
又捉摸著使出怎樣的手段才能鎮住阮夢玲,可思來想去的沒啥高招,還得去請教三叔。
他來到陳老三的船艙,卻見陳老三正揪著一個女人的頭髮,把自己的雞巴用力插進女人的喉嚨裡。
「靠,三叔你真老當益壯!」
回答他的,是陳老三迎面扔來的一隻拖鞋。
阮夢玲回到集裝箱的時候,方強什麼都沒問,不是他不想問,而是問過又怎麼樣呢?事情再明顯不過了。
阮夢玲一聲不吭地坐在他身邊,把從衣服裡掏出來的東西一股腦地塞給丈夫。
方強拿起一個湊在眼前仔細看了看,又聞了聞,才發現那是個蘋果。
整個集裝箱裡早不如起先的那般熱鬧,偷渡客們都沒了聊天的心思,無聲的沉默充斥著整個空間。
一開始船員來帶女人走的時候,還有人和他們對著乾,也有人怕得罪船員跑出來拉架,可時間一久,這股勁就散了,船員們再來的挑女人的時候,除了女人的家屬,基本沒什麼人會強出頭。
大柱子二柱子兩兄弟臉色難看的抽著煙,火燒火燎的旱煙味道熏得劉姐男人直咳嗽,可他也不敢抱怨,自打他攔著大柱子,不讓大柱子跟那船員打架開始,那兄弟倆就沒給過他好臉色。